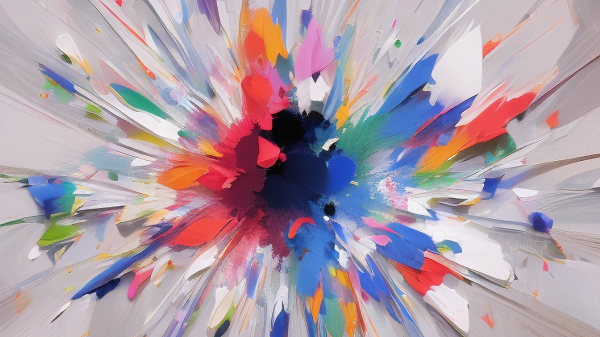
一站到席前,老杨头就失去了平静,尽管他事先准备了很久,甚至对着镜子演练过。可是此时,面对二十几桌客人齐刷刷的眼睛,老杨头只感觉四肢发抖,头皮发麻,心口发紧,脸上发热,幸亏这些年天天在户外跑着,皮肤仍保持着乡下人的黝黑,才不至让人看出脸红,可是准备好的腹稿却变得支离破碎,他只能一边努力回想,一边临时构思。他在城里生活了这么多年,可不能给儿子丢了脸。
“感谢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来参加我的婚礼……不不不,是我侄儿的婚礼!”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,却出了差错,客人们的笑声让老杨头更紧张了,特别是第二桌村西头李四麻子那一脸嘲讽的表情,他一边将眼睛转开,一边努力让自己镇定。
“我们这些年在城里——”老杨头忽然看到大儿子在看着他,猛地记起儿子说过不要讲太多在城里的生活。儿子说,那样的话会喧宾夺主。可他觉得儿子是怕他说出捡垃圾的事情。
那时,刚搬到城里,大儿子托了好几个人才帮小儿子联系到去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,日子过得很是窘迫。有一天,老杨头发现小区垃圾筒里总有一些纸箱子、塑料瓶之类的东西,他庆幸且小有些得意地觉得,终于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。从此,他经常会在小区各个垃圾筒边上转悠,每天竟有十多块钱的收入。他遂将领地扩大到了周边的几个小区,终于被大儿子发现。大儿子很严肃地列举了好几条不能继续的理由,说得最多的是不利健康,但老杨头觉得听出了儿子的言外之意。毕竟,这是公务员小区,很多人认识已经当上了副局长的儿子。他没有辩解,儿子刚参加工作那会,他还得意地跟别人说,别看儿子考上了大学,当上了公务员,但在家还是得听他这个当爹的。自从搬到城里,他就改了很多习惯,不再一天到晚叼着一根旱烟袋,不再随地吐痰,不再随便串门,大儿子也说城里有好多地方和乡下就是不一样。但直到回村前,他都没停止过捡废品,只是在有熟人的地方一定确认无人才动手,而且不论收获多少一定当天送到附近的收购站。前两年,小儿子换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,收入高了些,小儿媳也在一个家政公司找到了工作,有两千多元一月。他照常去小区里转悠,他打定了主意,老两口没退休金,没医保,没有城市户口无法申请低保,但他有一双手,只要走得动,就尽可能不增加儿子的负担。看着那些钱被丢掉不捡起来太可惜了,而且又不偷又不抢的,只要不影响儿子的面子,就没关系。那年,老杨头就在附近一家银行悄悄地开了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存折,现在上面的数字已到了五位数。看着那个仍在慢慢长大的数字,他心里已经在盘算,哪天小儿子真的要去买那套看上的二手房时,要给他一个惊喜……
老杨头看着儿子,停顿了一下:“我们这些年在城里生活得挺好,我看村里这些年变化也挺大的……”时隔十多年回到老家,他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农村,亲身站在堂弟家两层小洋楼前,他心里五味杂陈,有羡慕,还有一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妒嫉。他知道,在城里这叫别墅,至少要两万多一平方,随便一小幢都要几百万。老杨头记得堂弟的三个儿女曾用一个帘子隔开两个床,并排睡在一个屋。那年,侄女上中学了,实在觉得不像样子,不得已请家里堂兄弟们帮忙打地基,想加盖一间房,竟为了不到一米宽的地方与邻居陈家闹到了抡锄头扛菜刀,最后村支书出面还是将地基退后了半米。
“看着大家都过得这么好,我真想搬回来呀!”老杨头由衷地讲了一句心里话,马上又感觉到了大儿子紧张的眼神,刚刚平静下来了点的脑子顿时又一片混乱。
从省城到老家要倒三四次长途车,下车后还有五六公里的山路,老杨头自住到城里后没再回来过。几年前,大儿子买了私车,本以为回老家可以方便了,没想到老太婆晕车得厉害,坐上三五里路就要大病一场。他又不放心把一口乡音没人能听得懂的老太婆一个人丢在城里。这些年,就一直由儿子们清明回去扫墓。尽管儿子一直给他描述老家的变化,还拍了堂弟家新房的照片给他看,当时他只有满心为堂弟一家高兴。毕竟,被儿子接到城里住,老杨头心里骄傲着呢——那可是村里第一份的。比当年儿子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,后来又当上了副局长还要骄傲。他至今仍记得,搬家那天,村里人围观的围观,送别的差别,大家都说他是村里最有福气的。只是没人知道,近年来,他梦得最多的是老家的田间地头。此次回村,搬回来的想法更是强烈得不可名状。老杨头看着儿子的表情,他确定看到了一丝不安,立刻慌乱起来——他想不起刚才说了什么,但肯定说错了什么,越想理清,越是慌乱,只至儿子的脸越来越模糊……
宴席前排的客人清楚地看着老杨头的嘴巴一直在嗫嚅着,但什么也没说出来,至少他们什么也没听到,然后,在静静的等待中就见老杨头的身体向后倒去……
老杨头脑溢血去世,几天后,儿子们将他葬在了祖父坟旁,很长一段时间他又成了村里关注的焦点。(冀超)
华文国际网 版权所有 2026 © 邮箱:1351659001@qq.com